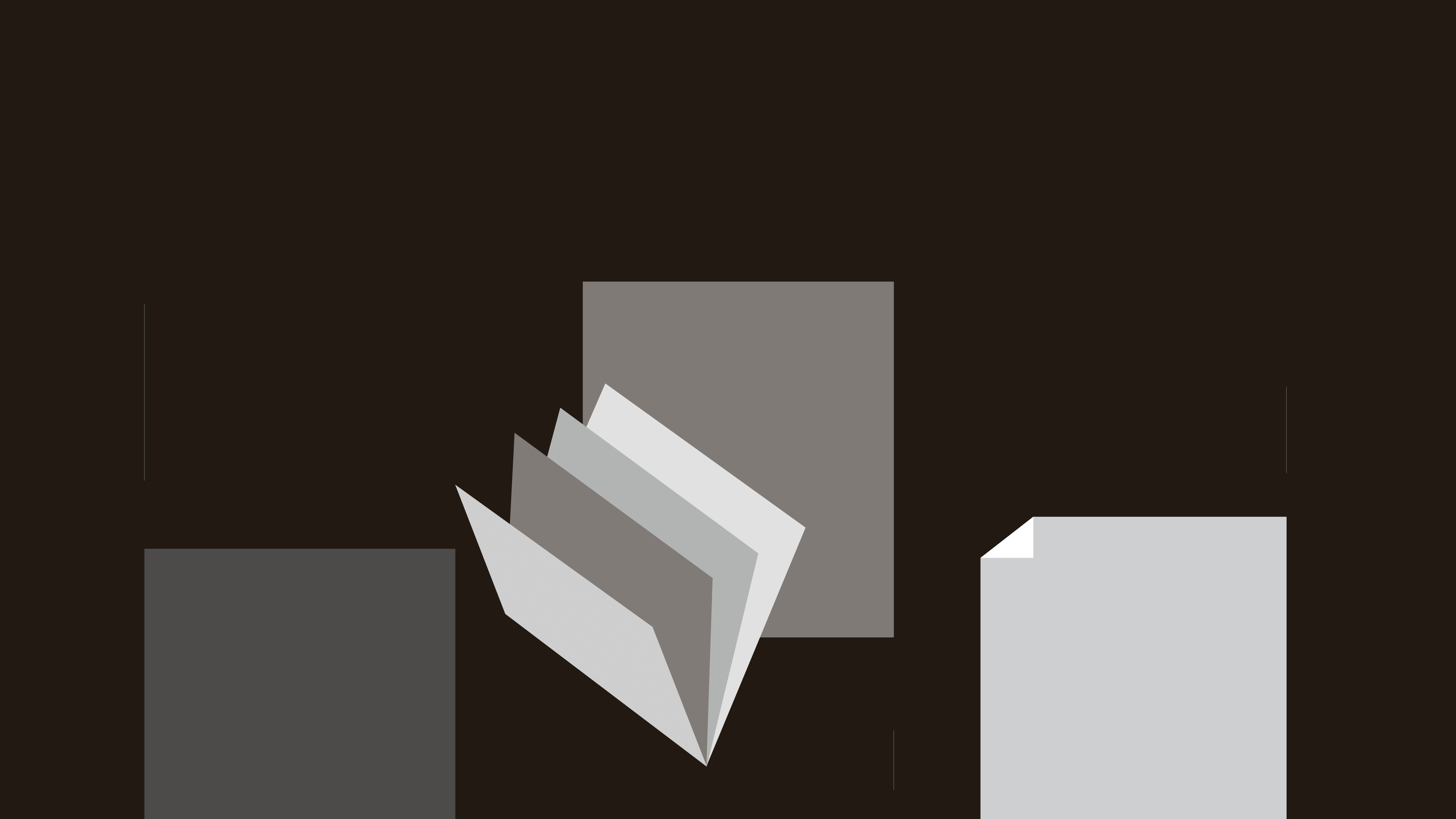杭州爱乐加入千人交响乐团 奏响国庆联欢
来源:
阅读:
作者:严粒粒 通讯员 甘佳钏 来源:凤凰网浙江 日期:2020-01-02
当《我和我的祖国》的最后一枚音符落下,成簇的烟花在靛蓝的夜空绽开。10月1日晚上,北京天安门广场陷入一片沸腾。
当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中,千人合唱团和千人交响乐团在广场上一同呈现演出,尚属世界首次。在中央和地方16支交响乐团1028人组成的千人交响乐团中,85人来自杭州爱乐乐团(下称杭州爱乐)。
从杭州开始追踪,直到今天深夜,我采访了多位乐团主要成员,感受他们的兴奋和感慨,聆听着许多背后的故事。
此次千人交响乐团邀请,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牵头实施。杭州爱乐名誉团长邓京山记得,7月中旬收到口头指令时,他正在杭州大剧院的会议室与同事开会。
“有机会参与国家的任务,是我们无上的光荣!”邓京山没有想过,这个成立仅10年的年轻乐团,竟有幸在国庆当天登上天安门广场的大舞台,“上一次杭州的文艺院团在此演出,已经是1958年的事了。”
献演过G20杭州峰会、曾赴匈牙利等“一带一路”国家顶级音乐厅巡演……杭州爱乐拥有丰富的演出经验,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
直到9月12日中午,乐团始料未及地收到第一次联排通知,要求第二天——中秋节当天抵京。乐团即刻向85位参演人员发出“集结号”:尽可能放下手里一切事情,收拾行囊,准备进京。
国之大庆,与有荣焉!在为小家团圆和为祖国庆生之间,没有人迟疑片刻。
收到通知当天,双簧管演奏员陈斯嘉刚与女朋友登记结婚,小两口决定婚庆事宜全部延期;第一助理首席胡兮正和父母在厦门度假,即使抱病,也即刻连夜赶回杭州;小提琴演奏员肖天言赴台湾看望许久不见的妻儿,飞机刚刚落地台湾机场不久,就挥别家人直飞北京……乐团还有不少双职工,在匆匆安顿好家中老人和孩子之后,便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10月1日下午,参加国庆联欢活动千人交响乐的杭州爱乐乐团全体演职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为国庆献演,不同的人体味着不同深意。“那可是天安门广场啊!以前就是个旅游目的地,今天就能在上面演出,简直做梦一样!”1994年出生的圆号演奏员刘金鑫年龄最小。年轻的他,最大的感受是兴奋。
使年长者彻夜难眠的情绪,却是万千感慨萦绕心头。中提琴首席赵宇年过五十:“错过这一次,怕是再有机会,我也没有体力了。” 后来他发现,千人交响乐团中还有位老艺术家年近七旬,考虑排演强度,上级曾婉拒他的申请。老艺术家经过申请再三,终才成其中一员。各地不少优秀乐手因为人数限制,退而争相申请作为幕后乐务人员服务演出。
中秋节当晚,杭州爱乐成为第一个抵达北京的地方乐团,也是千人交响乐团中唯一一个全员到齐的乐团。想起演出组组长第一时间向乐团表达的感谢,杭州爱乐党支部书记李亮仍掩不住激动与自豪:“他夸赞:‘杭州爱乐乐团能够顾全大局,星夜驰援京师,堪称楷模!”
在那现实版“明月几时有,千里共婵娟”的深夜,乐团几个年轻人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个小小的月饼,聚在一起分食。月光下,大家相互调笑“和同事共度中秋,机会实在难得”。

10月1日傍晚正式演出前,部分杭州爱乐乐团演职人员在千人交响乐团中。
9月22日,北京天安门区域和长安街沿线正举行群众联欢活动全流程、全要素、全力量演练。杭州爱乐再一次赴京参加联排。整个下午,乐团都在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进行排练。在天安门广场的正式联排几近凌晨才开始。
这天傍晚,大巴从酒店出发,穿着统一演出服的杭州爱乐团员们通过层层安检抵达天安门附近。“从大巴停靠点到演出台有1.5公里的路需要步行。有的乐器又大又重,还很昂贵,我们就这样抱着它们走进天安门广场。”乐团巴松管首席黄剑看见,一旁穿着高跟鞋的女乐手的脚歪了好几次,脚后跟也磨出了伤。
那天午夜,入秋的北京气温跌至不到20摄氏度。大风扫过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4个小时的等待、演出、散场时间里,乐手们扛着低温,严阵以待……男乐手的丝绒西装尚能御寒;女乐手身着单薄的礼服,身上起了不少鸡皮疙瘩。
如果说,当晚广场联排的低温尚且让乐手们感受真实;那么,今夜正式演出时,全情投入下的热血奔腾感受,简直如梦似幻。
“你能想象那个浩大场面吗……没有一个演出舞台、没有一个国庆假期,会比今天的更加难忘!”韩斐说,此时此刻,所有人都在享受这个彻夜难眠的晚上。
《红旗颂》是演奏曲目之一。乐曲的引子由小号奏出。想起之前韩斐提起,正式演出前的一次联排后,小号首席姚天浩曾经拍着他的后背,默默感慨“号音一鸣,眼泪差点飚出来”。
“今晚他哭了吗?”我问。
“今晚他真哭了。”韩斐说,“我也是”。